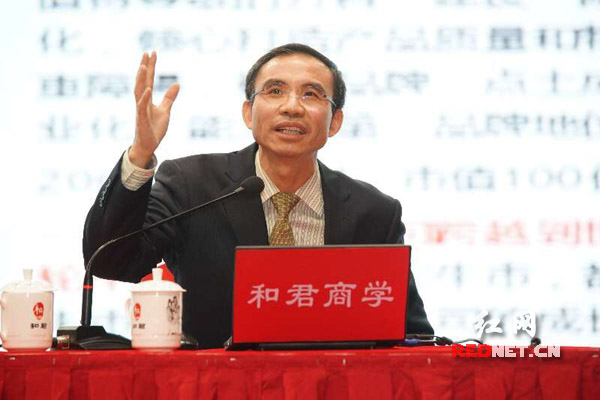近日,正值中国恢复高考40年的高考日子。和君集团董事长、和君商学院院长王明夫专门撰文,饱含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三十几年前那段高考的历史,并由衷发出“人生中最震撼人心的奋斗,莫过于高考的奋斗”!
【中美创新时报波士顿6月7日讯】(记者温友平)近日,正值中国恢复高考40年的高考日子。和君集团董事长、和君商学院院长王明夫专门撰文,饱含深情地回顾了自己三十几年前那段高考的历史,并由衷发出“人生中最震撼人心的奋斗,莫过于高考的奋斗”!从历史意义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开始的。从此,中国高考这根“指挥棒”开始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并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40年来,中国高考不但承载了整个中国不断向前发展的使命,更承载了数以亿计的青年通过高考而通向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历练与记忆。如今,中国高考显然已经进入到了发展到了从单一到多元、从精英教育迈向大众教育的现代教育阶段。很显然,王明夫于1984年参加高考并以全县第二且政治单科成绩全省状元的优异成绩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当属于中国高考单一、精英教育一代。
真可谓“英雄均有出处”。作为中国恢复高考最初阶段的农家子弟,要飞跃“龙门”,更是需要经历更多的磨难,其实这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国磨难的一个缩影,折射到王明夫一类整天向往着山外世界的农家孩子们来说,他们纯净得像一张白纸的内心深处,往往又更有爆发的力量。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成功之处。于是,王明夫高考的成功并在日后继续的研究生深造,为他之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研究生毕业的王明夫只身南下深圳,而此时的深圳正是在南巡春风吹拂下迎来的二次创业阶段,可以说,王明夫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好的时代。尽管王明夫在经历了露宿深圳荔枝公园的求职“艰难”后,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同是当初全县高考状元同学的帮助,以此顺利地走上一条金融业发展之路,并最终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得到了“如鱼得水”般的历练,成为为当今中国乃至亚洲最强的咨询企业集团掌门人。
无疑,王明夫的成功,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改变中国命运和数以亿计青年成功人生的一个“样本”。正鉴于王明夫的这个“样本”意义,美国华文新锐报媒《中美创新时报》在此特编发王明夫所撰写的以下长篇文章,以飨读者(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
人生中最震撼人心的奋斗,莫过于高考的奋斗
王明夫/文
童年生活,饥饿、寒冷、苦累是留给他的最为深刻记忆
每年高考时,我都会想起三十几年前我的高考。高考对命运的意义,得从我的出身开始说起。
1966年,农历马年年初一晚上,我出生在江西省会昌县周田乡上营村一个传统农家。
上营村,座落在武夷山西部余脉的一个山间盆地里,张目四望,周围皆山,是绵延不绝、黛青一色的群山。山外世界是什么,不得而知。隐约知道,北边的山那边是会昌县城,东边的山那边是福建武平,南边的山那边是广东梅县,我都没去过,也不能想象这辈子能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16岁去县城读高中,走出这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山间盆地。16岁之前,视界最远就是这个山间盆地四周的山顶。这里长大的孩子,不是井底之蛙,但百分百是盆中之人。大山隔绝了他们跟外面世界的联系,也保住了他们自然生长的天性,狭隘与纯朴,愚昧与本色,坏与好,都在其中。我一生的打拼和闯荡,好像都是为了走出这里,但从来没有熄灭过对这里的归意。
上营村是传统的客家人村落,世代农耕,种田砍柴,牛犁田,狗看家,我童年熟悉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与生活方式,与书上描述的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无异。放牛、放猪、放鸭子、打鱼草、拾粪是我童年的日常工作,年龄稍大点,十岁左右起,就上山砍柴、下田耕种、挑担赶集卖梨子卖糯米卖甘蔗。
童年生活,留给我的最深刻记忆,一是饥饿,二是寒冷,三是苦累。每年总有那么几个月,家里是“冇米”的,红薯是救命的主粮,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连吃二三个月的红薯。假如没有红薯,大概童年时候就饿死了。那种时候,有一碗糙米饭吃,不需要任何菜,来点酱油、滴点香油,就觉得特别享受。记忆中,童年的冬天,总是阴雨连绵、寒风刺骨,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到身上了,一整个冬天还是冻得无所躲藏。南方阴冷的冬天,一个人冻得无所躲藏的时候,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想大哭的感觉的,只能自己扛着受着,贯穿整个冬天。
至于苦累,莳田、割禾、挑担、砍柴,其劳动强度,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说,也就是身体承受的极限了。以上山砍柴为最,一大早天刚蒙蒙亮,被妈妈嚷醒,急急地吃罢早饭或没饭吃的月份就吃红薯,然后磨柴刀、穿草鞋、操起扁担柴络,跟着一伙大人往山上进发,走十几里山路,在荆棘密布的野山里搜山找柴,看中一棵树,砍倒,截段,装担,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了。人小,力气不足,干活慢,装担刚完,还没喘过气来,同行的大伙谁喊一声“走”,我就得马上挑起担子跟上,否则大人先走了,一个小孩掉队,心里非常害怕。山里看见蛇、野兽、野鸟,听见不知名的怪叫或响动,是常有的事。我很好强,总是想多挑点柴回家,尽自己的极限。挑着柴担子,跟上大人的速度,往回再走十几里地,快到家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午后太阳西沉时分了。六七个小时过去,中途没有任何食物补充。离家最后剩几里路远,非常的饿、非常的累,实在是不剩什么体力了,眼巴巴望着家里人来接担子。不时地有村子里谁家的人先来接担子了,我就要问看见我家人了吗,谁来了,走到哪里了,快到了吗?远远地看见妈妈或家人来接担子了,心里一下就得救的感觉。家人接过去柴担子,我吃着家人带来的充饥东西,跟着走回家。终于到家时,整个人就瘫倒在屋壁下的石板上了。第二天,继续。日复一日。
小学阶段,从“书还冇到”到最早的政治事件记忆
我的父亲母亲,都没上过学,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父母亲是1920年代生人,我的小弟弟出生于1971年。想想看,1920-1970的年代区间,中国除了战乱,就是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我家乡那里是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核心地带,红军长征从那一带出发,红军远走后是国民党报复的重灾区,后面是抗战和内战时期。解放后就是历次政治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等等。整整半个世纪,老百姓几乎没有多少休养生息的喘息机会。在中国历史的这个区间,一对不识字的农民夫妇,在闭塞的山间盆地里,要养活自己和一群孩子,不至于饿死病夭,那种劳作之艰苦卓绝、生活之穷困艰难,我后来任何时候想起,都有一种瞬间就要泪流满面的冲动。
我在虚岁六岁的时候,就自己闹着要上学,大人没允。虚岁七岁入学上营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成绩拔尖,班里第一,是三好学生,个个学期都拿奖状,奖品是崭新的铅笔和笔记本,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三年级四年级成绩一落千丈,一塌糊涂,个子也瘦弱,凶狠的同学可以随时随地欺负我、恐吓我,孩子王拉帮结派,我总是落单的,孤零零,感觉随时都会受到攻击。他们骂我或踢我一脚啥的,我就眼泪汪汪,强忍着不让眼泪下来,心里压抑着愤怒和报仇的冲动。
我读小学的时候,经常是学期开学很久了但“书还冇到”(我们管课本叫书),老师也不知道教什么。每当“书还冇到”的学期,老师上课就让我们背诵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等等,至于那些诗词的意思,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的。另外,老师还教我们唱歌,其中有一首歌,几乎唱了半个学期,叫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现在都还会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来知道,那不是音乐课,那是所有课。半个学期过去了,书终于到了,歌才止唱。四年级那年,毛主席死,上营村的王氏宗族祠堂里设了灵堂,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吊唁,一条黑布白字的大横幅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永垂不朽”这个词儿。气氛很严肃,很静穆,大家默哀3分钟,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有人哭泣,我受感染跟着哭,不明就里。我不敢出声,就是跟着走,跟着做。后来学校组织师生步行几公里去公社(圩镇)大礼堂吊唁,也一样,静静地进去,默哀,鞠躬,静静地出来。没过多久,上营小学的全体师生排队步行去公社迎接华主席像,一个同学举着华国锋剃着寸头的那个标准像,一个同学举着旗帜,还有些同学则负责敲锣打鼓,一路热闹。我是属于跟在队伍里的“群众演员”。N个月后,老师又组织大会,宣传打击右倾翻案风,打倒邓小平。又N个月后,敲锣打鼓粉碎四人帮。这些,是我此生关于政治事件的最早记忆了。
初中阶段,成绩从一塌糊涂到留级复读时的一马当先
五年级小学毕业,我去邻村上初中,是一所乡村中学,叫做半岗初中。初一年级,成绩一塌糊涂,大个子同学随时羞辱我,给我取很难听的绰号,我狠不得砸死他们,终究也是没有勇气做任何反抗。数学期末考试不及格,印象中才20几分,留级。我羞于重回学校,不想再上学,回家去学裁缝。缝纫机都买了,师傅也基本确定。我的大哥从深山老林里搞副业回来,发现我不上学,态度坚决、不容商量地把我骂回了学校。于是我硬着头皮去复读初中一年级。莫名其妙地,成绩像魔术一样变得奇好,尤其是数学成绩,雄霸整个年级。全县初中一年级数学竞赛,我得了周田公社第一名,张大红榜在周田圩镇上。这是半岗初中有史以来的崇高荣誉,校长召集了一个全校师生大会,亲手给我颁发了一份隆重的奖金,3元人民币。这是我少年时期最伟大的一次胜利,尊严和自信,拔地而起,昂首矗立。从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数一数二,直到高中毕业。同学欺负我、羞辱我的情况,没有了。我变得受到同学们的仰慕。从一二年级的成绩出众到三四年级的烂得一塌糊涂、从初一年级的成绩一塌糊涂到留级复读时的一马当先,我的学习成绩,为什么会这样陡变,至今也想不明白。
因为初一留级,我初中念了四年,1977-1981年,住校,周末回家,周日傍晚返校的时候带足一周要吃的米菜。那时农村政策已经搞联产承包,我家粮食已充足,带多少大米去学校,父母是让我随意取的。所谓菜,就是我一周要吃的下饭咸菜,基本上是一搪瓷缸子的菜干(霉干菜)或芋荷(腌渍成酸的芋头苗梗),四年时间,几乎都一样。几十年后母亲说起,还是总要说到,我初中带的菜,总是苦巴巴的干涩,她炒菜的时候想多放点油水都没油。那时候,如果有一瓶酱油浸生辣椒,我一周都会饭量大增。四年初中,12-16岁,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饮食度过,个子一直没怎么长,很矮,很瘦小,脸色枯黑。上高中的时候去了县城中学,伙食改善,一个学期下来个子就窜上去了,长到一米六多,第一个学期结束回家,家人几乎不敢相认。
我中考很成功,是当年半岗初中唯一考入县城高中重点班的学生。其实,我那时特别希望考上中专,去读师范学校。读中专,就是确定性地跳出了农门,这已经是最惊天动地的奢望了,不敢去做梦上大学。以往,最好成绩的考生,总是去读中专的,我为什么没去,据说是那年开始,县教育局有意识地把尖子生选拔进县高中重点班,以代表县里去冲刺考大学。16岁,我去县城入学会昌一中,开始了离开农村的城镇生活。
入读重点高中,充满了人生的憧憬和向望
这是我出生以来的一次历史性跨越,进城了,感觉非常的新鲜、非常的高级、非常的自豪,充满了人生的憧憬和向望。连县城马路上汽车经过卷起的尘土夹杂着汽油味,我都觉得是香的,一种乡村少有闻到的新鲜气味。城里的女人都穿裙子,居然夏天还穿袜子,真洋气;男女同学之间,即便是异姓,也是可以讲话甚至交往的。这些现象,让我感到明媚,升起游丝般的憧憬。
高中的教室是日光灯,白花花的,超级明亮。我自出生以来,从来没有在夜间感觉过这样的明亮。乡下的夜间,用煤油灯照明,为了省煤油,灯是不愿意挑到明亮程度的。小学的时候,我如果夜间看书,父亲是要骂的,因为耗煤油。父亲说,你如果会读书,学校里就读好了,为什么到家里还要读?你如果不会读书,点灯读书又有何用?父亲的逻辑,无懈可击。半岗初中的时候,一个教室几十个同学,每人点一盏煤油灯上晚自习,几个小时下来,整个教室乌烟瘴气,同学们熏得浑身都是煤油烟味儿,脸色和鼻孔发黑,咳出的痰都是黑色的,回到宿舍用毛巾抹一把脸,毛巾都变黑。初中几年,夜复一夜皆如此,我们安之若素,习以为常,也没听说过有谁因此不适或生病。这种状况,倘若放到现在,必有好事者、自媒体啥的,做自作多情地的无尽渲染,引发一场全社会范围的舆论风潮或捐助运动,也说不准。而那个时代,全国各地的乡村学校,大多是这样的。我进到县城,到处有电灯,连自己的宿舍都有电灯,感觉很高级。尤其是高中教室挂着足够多的日光灯管,那种明亮,动人心魄,终生难忘。不好好学习,感觉都对不起那日光灯。
我高一开始学英语课,是从初一年级的第一册英语课本学起。此时我始知有所谓26个英文字母之说。用汉语注音读英语词句,书上的thank you我就注音成“三克友”,how are you我就注音成“好啊友”,等等,是我高一时候的英语起步方法。第一学期期中考试,英语成绩很差,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期末考试,我的英语成绩就名列前茅了。高一时候,我的成绩在整个年级里都是居前的,班上则稳居前三,数理化三科尤好,尤喜物理。高二开始分文理科,我选了文科。那时候,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理化成绩好,是高人一等的,基本上选理科。我数理化拔尖,为什么选文科?听说文科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理科低很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大学,至于文科理科、本科专科、什么专业、什么学校,一概次要。我,我家人,最高的、终极的愿望,不,不是愿望,是想入非非、胆大包天的奢望,就是出个大学生。文科录取分数低,应该是更容易被录取吧,于是我选了文科。我选什么科、上什么学,家长是不会过问的,也不会有哪个老师来关心我,懂和不懂、对和不对,都我自己定。一个对人生、对社会、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懵懂少年,自选走向、自安天命。
事后证明,我选文科是对的。我自考往届的文科高科试卷,数学卷子对我来说很容易,我不复习都能考90多分。于是我高二开始,基本上不用学数学,省下一个科目的学习时间,用于主攻其他五科。很多学文科的人,都被数学拖得死死的,占用太多的时间,我却把全部时间集中到了其他科目上。其中,我的历史地理英语政治科目好,语文最差,尤其是写作文,文思枯竭、无从下笔,每遇写作文,就头痛。论总成绩,高二高三,我始终保持班里第一第二的位置。
高中期间,我每月的生活费是15元,平均一天5角钱,伙食费是大头,一天三顿饭,我通常是二顿素菜,芋仔(芋艿)、包菜、豆豉辣椒,吃得最多。菜金是5分钱一顿,豆腐则一毛钱,二顿合计一毛至一毛五分钱。吃一顿荤菜,主要是肉片炒包菜或肉片汆豆腐,偶尔小炒鱼块(传说中的赣南小炒鱼),菜金2-3毛钱。打饭就管饱,月初就买足饭票,不作节省考虑。有一次,和两个同学合伙,三个人凑钱买了一个苹果吃,每人一口,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苹果。当晚做梦,都还在回味苹果的滋味。
我每月15元的生活费,家里总是准时给到。父母、大哥大嫂、二哥二嫂,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一切经济来源,靠他们劳动而来。父亲和大哥当家,每年,每月,首要的盘算,就是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怎么来源,这是他们严防死守的兜底事情。种植什么、啥时候收成,养殖什么、啥时候出栏,啥时候卖钱,家用花销怎么预算,都是要通盘计划、应时而动的。如果出现稻子歉收、禽畜得瘟疫、集市价格下跌、家人突发大病要发生医药费等情形,预算中指望的钱就要掉链子,这是十分紧张和压力山大的事。猪得病了,涨大水把鱼塘淹漫了、鱼跑了,鸭子丢失了或死了,这些情况的发生,全家人的痛苦和紧张,那真是甚于死人。我童年时候放鸭子,鸭子误食农药浸过的谷子,眼睁睁看着鸭子一只一只地软腿、晕转、断气,我跪下去哭过。
父亲和大哥主持家政,因为要供我和弟弟(其时在上初中)上学,坚持不分家,全家人团结合力,只为供养我能念完高中。父亲和二个哥哥约好,等我高中毕业再分家。有一个月我的伙食费,被人撬了宿舍的箱子给偷了,我眼泪哗啦就下来,止不住,非常的难过。家里听说后,及时又寄来了生活费,没有丝毫责怪我。校保卫处来破案,抓了一个同寝室的嫌疑同学去审问,他死不承认,案子终究不了了之。
五个高中同学,对我的一生很重要:刘义林、罗庆丰、蔡伟林、肖世优、许地长。刘义林是我高中和大本时期的精神领袖和心灵明灯,罗庆丰是我上海读大学时候相依为命的精神导师(他念复旦大学法律系),他俩的才学志趣、阅读范围、思想情怀和忠厚人品,是我那个阶段的主要开化和精神涵养,他俩对我的精神成长的影响和意义,是我人生导师级的。蔡伟林是我高中时候的同床,他家出被子、我家出席子,我俩睡一个被窝,直到毕业。我们全班同学几十个人,住一个大教室,像是大通铺,每二个人一张床,家境好点的出被子、家境差点的出席子,二人一个被窝,相互温暖。班主任张景星老师是个大好人,每到冬天,就让我们去他家拿稻草,要多少就可以拿多少,铺在席子底下,暖和。上大学后,历次寒暑假我从上海回家,途径南昌中转,第一站落脚吃住,一定是去江西师大找蔡伟林,吃他的,住他那里,宾至如归。所谓发小或闺蜜,大抵如此。肖世优是高考我第二、他第一的同学,他是我人生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一个贵人和恩人。1993年我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去闯深圳,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睡荔枝公园,是他帮助我在深圳找到了工作、站住了脚,一手引领我进入了金融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处境和轨迹。肖世优的头脑、智慧、理性、敏锐和对问题本质的洞察力,迄今都是我只能望其项背、永远难以企及的。现在,我遇人生大事,自难定夺的话,还是会下意识地想到去找他问意见。许地长是我高中同桌,后来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搭档之一、真正风雨同舟的战友,我创业时候他是跑办工商注册手续的第一个员工,从此我们共事十几载,顺逆不弃、和衷共济,他总是以和君大局为重,任何情况下都配合我、为我分担、尽其所能扛起责任,不伪不妄,不矫情,不做作,无私心,像个劳模一样勤勉尽职、默默担待,成为了和君集团的重要管理者,对我的事业,贡献很大。
“一切为了高考”,实现有效的自觉和自律
高二开始,一分文理科,我就自觉进入了“一切为了高考”的状态。学习很有计划性:数学不用学,省下时间;历史,地理,政治,甩掉老师的进度,自己通读,来回重复读,算好重复多少遍就可以记住,由此明确每一章节内容需要重复多少个来回、用多少时间;英语就跟着老师的进度走;语文,凡是能死记硬背的知识,就死记硬背,作文就听天由命,不知从何学起,基本放弃,不想多花时间去搭理。我把学习任务,分解、均摊到每一天每一周需要完成多少学习量,然后每日每周都去完成它。有时候也会厌学,就是不想看书,就是读不进去,但我总能倔强地克制自己完成当天的任务。完成之后,就去校园玩,放松,运动,换心情。看上去我经常玩,但成绩又很好,显得学习很轻松。实际上就是计划明确、日清日毕、心里有底、不急不躁,考试成绩则水到渠成。
没有谁指点过我学习方法,也从没有看过这类的书籍或文章,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类书籍和文章,我的学习怎么会进入这样自觉的状态,至今也纳闷。体力决定精力,精力决定效率,为了适应学习的需要,我十分重视锻炼身体,沿校园外的田埂跑步,每日长跑,日复一日,像是必修课,无人督促,自觉为之。感谢上帝,让一个懵懂青年在他对一切都还懵懂无知的时候却对一件决定他人生命运的超级重要事情(学习)实现了有效的自觉和自律。
1984年高考,我大获全胜,总分531分,全县第二名;政治90分,为江西省单科状元,上了江西日报;数学正好100分;语文最差,80分出头。出成绩的时候,正是暑假农忙季节,我从农忙中抽出时间,坐长途汽车去县城看成绩,当我得知成绩后,欣喜若狂,幸福无比,所谓“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我以第一时间第一速度,速赶回家,全家人正在田野里莳田(插秧,种秋季稻),我远远就喊:我考上大学了,我真的考上大学了,我真的考上大学了。全家人,父亲、哥哥、嫂子、姐姐,听到我的喊声,都直起腰,望向我,惊疑而木然,像是一尊尊雕塑,植在田野。那一刻,好像整个田野、周围的群山、环绕的河流,都定住了,苍天感慨,万物肃然,整个田野回荡着一个祖祖辈辈世代农家的梦想突然花开的声音。家人谁第一个发声,就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我真的考上大学了,是全县第二名,肯定考上了重点大学。于是,田野沸腾了,群山含笑,河流奔腾。全家人的劳动,变得异常的欢快、喜悦、利索、有劲。
人生中最震撼人心的奋斗,莫过于高考的奋斗
我的高考,已经过去30多年了。直至今天,每年高考的日子,我都有一种忍不住想流泪的冲动。在我的人生中,最震撼人心的奋斗,莫过于高考的奋斗;最伟大的胜利,就是高考的胜利,没有之一。
高考,是决定无数人无数家庭命运的重大关口。我想,我若是一个高考教练或高中老师,我肯定能够辅导很多人顺利闯过这个关口,无非就是三条:第一,明确学习内容;第二,制定学习计划,分解、均摊学习任务,日清日毕、周清周结;第三,管理饮食、作息、运动和娱乐,保障营养、睡眠、体力和心情。这是个化繁为简、纲举目张的“三条军规”。我总觉得,一个高中,按这三条来全面改造教学计划、学生管理和校园生活,可望批量生产高考赢家。现有的技术手段,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多媒体、声光电、VR/AR、AI等等,还可以把这三个维度的要求,转化为随时随地、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的高考生活,告别苦逼高考,奔向炫酷高考欢乐高考。如果哪天和君出手做课外辅导、高考经济或者直接兴办中学,我料定能大获全胜。只是现在的我,实在不愿意去做应试教育。
很多人都以为高考竞争是较量智力,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智力落差太大的人之间,不构成竞争关系;构成竞争关系的人之间,胜负决于自我管理,跟智力水平弱相关。
何止是高考,人生每一个阶段的重大目标,都可以这样达成,水到渠成:第一,树立目标、明确任务;第二,制定计划、分解任务、日清日毕或周清周毕;第三,管理自我、健康身心。整个人生的成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今年51岁,回望自己的半百人生和观察很多人的状况,发现这是贯穿一生都有效的成功模型,无妨称之为“TPS模型”(Task-Plan- Self discipline)。
用TPS模型当镜子来照一下自己,自己能否达成人生某个阶段的目标、实现所谓的成功,结论是分明的,问自己三个问题:我能正确地识别任务吗?我能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吗?我能自我管理、执行计划吗?三缺一,成功无望;三缺二,基本就别扯了,洗洗睡吧。前二者,是可以借助外力来做到的,比如高考这件事,遇上好学校、好老师、好家长、好咨询,帮你识别任务、制定计划,但最后一条,自我管理,是上帝都帮不了你的,如果你自己不能进入状态的话。我凭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可以肯定地说,自我管理,永远是人生成败最最要害的分水岭。李嘉诚说过大意这样的话:很多人的处境不佳或人生失败,本质上都是自我管理上的失败造成的。此言虽过,但有理和警醒。
我们那个时候,上个世纪,1984年,高考填报志愿是在考试结束后、分数出来之前完成的。考完了,我只知道自己发挥正常,成绩多少,不知道。填报志愿,也没有任何人指导,家长是肯定不会有任何要求的。我自己是懵懵懂懂、稀里糊涂的,因为出身农家,所以本能地想报考农业大学;因为童年时候觉得穿白大褂的医生很高级,所以又想报考医学院。直到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才得知农学和医学专业,属于理科,文科不能报。可想而知,高中毕业时候的我,见识浅陋到什么程度。
我的主要志愿,都是沿着师范系列填报的,第一志愿华东师大,因为它在上海;第二志愿江西师大,因为它在省城南昌;第三志愿赣南师专,因为它在地市赣州。专业上填报了英语专业和政教专业。我总分达到了可以进入中国任何一所最好大学的水平,政治又是省里状元,当然是被录取进入了华东师大政教系政教专业。我情有独钟师范大学,并不是我喜欢做老师,也不是我知道上师范大学对人生意味着什么,而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唯一近身接触过的非农职业,就是“教师”,那些从小学到高中给我上课的老师们。除师范外,我对其他的各类专业院校,基本上闻所未闻、浑然无感。一个农村孩子,从农家生活到县城高中,从低年级课本到高年级课本,从应试到应试,就是我的全部阅历和知识范围,我能知道啥呀?连迷茫和困惑我都没有,我只有混沌和无感。
今天看来,我当初的无知无感,是一种竞争优势、制胜法宝,因为它保障了我没有多余的关切和分心,没有思想世界的困惑、心灵情怀的扰动和花花世界的诱惑,我只专注于一个目标:那就是高考。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改变我的命运,而其他的,都于事无补。人生是分阶段行进的,任何一个阶段,专注于那个阶段的最要害命题,集中自己的全部心力、智力和体力,牢牢地扣死它,彻底地打穿它,压倒性地完胜它,这几乎可以升级为人生战略战术论。我的高考,就是这样。